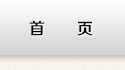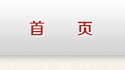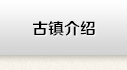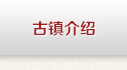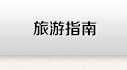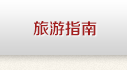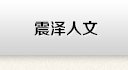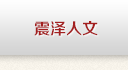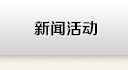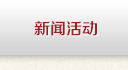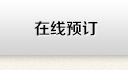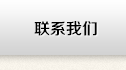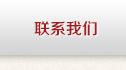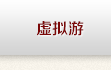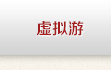人生不相见,有时交臂失之,地域、景观也是一样。苏州的古镇震泽,我曾几次从她身边擦肩而过,但都错失了会面机会。1984年,我在东北某一城市工作,曾到苏锡常一带学习改革开放、经济发展的经验,到过震泽所在的吴江;后来,两次去周庄、同里,还到过和震泽紧相毗邻的南浔,却偏偏错过了这一古镇。也许人生真的存在缘分,这次机缘到了,参加作家采风团,出了浦东机场,乘车直奔震泽。相逢一笑,契阔平生,深抱相见恨晚之憾。
一踏上这片土地,脑际便跳出来两句古诗:“输他震泽名偏古,禹迹犹传底定桥”。此间地处吴头越尾,唐开埠,宋设镇,清置县,确是有足够的资格,当得起“古镇”这个称号。至于同周边一些地方较量水乡风光、自然景色,总是各有所长,难为轩轾。我这里想着重从历史积淀、人文景观角度,谈谈她的特色,说说我的观感。
早在宋代,此间即振兴儒学,立明教堂,建震泽书屋,祠奉三位名贤,一时学风蔚然。明清两代,尚文重教之风尤为鼎盛,书院、义塾、私塾,遍布全镇。清人徐丙华的诗句:“书楼遥望遍桑麻,比户相连耕读家",正是当时的真实写照。因此,历代人文荟萃,才俊辈出。区区一镇,出过十五名进士、二十二名举人、三十八名贡生。远至清末民初,这里又首开创办新式教育之先河。光绪年间,即有女校出现:上世纪二十年代,镇里就办起了中学,独占全县鳖头。
采风的最后一站,是始建于元代的获塘河上的思范桥。“范”即春秋时识机在先、功成身退的范蠢。镇上关于范蠢的遗迹,还有蠢泽湖、范蠢祠和范蠢故居、范蠢钓台遗址。这里,咏赞他的诗甚多,清人程礼有句云:“会稽霸业十年成,鸟尽弓藏意独行。”这使人联想到震泽在人文方面的另一个特征——盛产逸民、隐士。在清人辑集的“震泽八景”中,除了“范蠢钓台”,还有隐居江湖、自号“烟波钓徒”的唐人张志和的“张墩怀古”;宋代震泽三贤的“复古桃源”;明代不合于时、解组归田的吴秀的“康庄别墅”,整整占去了一半。王锡阐本身就是一位明末遗民。他穿古装衣服,写时人不易辨识的篆字,生活中不使用清朝钱币,著作中不标识大清年号。故国之思、亡国之痛,伴随着他的整个一生。从其晚年所赋《绝粮诗》中:“尽道寒灰不复然,闭关岂复望人怜!平时空慕荣公乐,此后方知漂母贤。何必残形仍苟活,但伤绝学己无传。存亡不用占天意,矢志安贫久更坚。”可以看出他的气节和抱负。
隐逸之风,在当地士入中表现为,一是看重名节,义有所不为,于进退去取不苟且行事;二是淡化官本位,热心实业。而它之所以在震泽盛行,不外乎三种因素:其一,自古以来,此地即安定、富庶,而且风光秀美,民风敦厚,文化底蕴丰富,又兼自古即有范蠢归隐的佳话流传,遂使后世遁迹江湖、疏离政治者择为首选;其二,清初著名文字狱“庄氏史案”发生于近在咫尺的南海,本镇也有几位名士身被其祸,其腥风血雨犹彰彰在人耳目,遂使大批士子绝意功名仕进,纷纷遁入民间,或隐居不仕,或投入陶朱事业,走当年范蠢的路子;其三,此地盛产蚕桑,商业经济发达,官本位观念相对薄弱,热心实业以及文教、科技者甚多,这更是观念更新、社会进步的实际体现。
师俭、重德,显现出一种人生智慧与文明根性;尚文重教、热心实业而淡化宫本位,代表一种道路抉择;而看重名节,不轻忽于去取出处,则体现一种生命价值。这些都属于精神蕴涵,深层次的理念,都是纷纭万象后面的本质呈现;特别是在重实用轻理想、重金钱轻道德的消费时代,更有其针对性很强的现实意义。誉之为“古镇灵光”,不亦宜乎?
 |
(王充闾,辽宁省人大副主任,著名作家,著有散文随笔集《柳荫絮语》、《人才诗话》、《清风月白》、《沧浪之水》、《春宽梦窄》和诗词集《鸿爪春泥》,学术著作《诗性智慧》等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