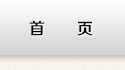1958年3月在浙江吴兴县钱山漾遗址的发掘中,出土了4700年以前的丝带、丝线及绸片;1959年梅堰又出土纺轮、骨针、陶罐多件,其中黑陶罐上刻有丝绫纹及蚕形图案,据文博部门鉴定系属新石器时代文物。由此推论,当时太湖沿岸地区已有原始的缫织劳动,再从陶器上的蚕纹推知,生长在原始桑林中的野蚕,已为初民所喜,蚕蛹既为美食,茧壳更可制绵、抽丝以蔽体,造福于人。
1958年3月在浙江吴兴县钱山漾遗址的发掘中,出土了4700年以前的丝带、丝线及绸片;1959年梅堰又出土纺轮、骨针、陶罐多件,其中黑陶罐上刻有丝绫纹及蚕形图案,据文博部门鉴定系属新石器时代文物。由此推论,当时太湖沿岸地区已有原始的缫织劳动,再从陶器上的蚕纹推知,生长在原始桑林中的野蚕,已为初民所喜,蚕蛹既为美食,茧壳更可制绵、抽丝以蔽体,造福于人。
钱山漾在西,梅堰在东,地处太湖南岸的震泽地区,其实早在新石器时代已从事蚕桑生产。相传晚唐诗人陆龟蒙曾寓居在震泽左近,其诗作中有“桑柘含疏烟,处处倚蚕箔”及“尽趁晴明修网架,每和烟雨掉缫车”之句,足见当时震泽地区之养蚕缫丝业已经相当普遍。
震泽蚕桑业的大发展得益于明初朝廷推行的鼓励农桑政策,其时1亩桑田的收益抵得上10亩稻田。于是无家不蚕,形成举足轻重的家村副业,以至乡村间“绿荫弥望”,几乎无闲田旷土。震泽及附近的古石桥楹联上有“桑麻蔽野”和“农桑兴大利”之句,足可佐证。
震泽乡民对蚕桑业之依赖远甚于农耕,道光《震泽县志》说“凡折色(漕粮)、地丁(地赋、丁赋之合称)之课及夏秋日用皆惟蚕丝是赖,故视蚕事綦重。”历来震泽地区就有“春茧半年粮”之说,春茧收入除了日用开销外,还供以秋熟作物的农本。《慈云塔影》诗句“蚕事胜耕田”,一言中的。乾隆《震泽县志》亦云:“丝之丰歉即小民有岁无岁之分也。”
震泽蚕农不辞“辛勤瘁苦”,积累了丰富的育蚕缫丝经验,如道光《震泽镇志》记述:“丝有头蚕二蚕,较他处更光白……”成为湖丝中之精品,而辑里丝问世后,更是蜚声海内外。清光绪六年(1880),震泽一地出口的辑里丝达5400余担,占半年全国生丝出口总量的十五分之一弱。
近代,为适应国外丝织工艺的新要求,震泽人又将辑里丝加工摇制成辑里丝经(又称干经或洋经)出口,据《农工商报》载“民国初年(震泽)境内摇户(加工丝经的专业户)约一万数千户,男女人工十万左右。”丝经业兴盛了近百年,双杨村及其他蚕区宣传土丝改良。
同年夏,在开弦弓村开办吴江县震泽市、省立女蚕校推广部合办蚕丝改进社。翌年,复在镇上慈云塔寺院内举办制丝改良传习所。以后,蚕丝合作社和蚕丝改进社几乎遍及震泽区每一个乡村,使蚕丝业得以更上一层台阶。
1929年,在震泽镇东栅开办震丰缫丝厂,职工近千,为吴江第一个产业工厂。同年,开弦弓村有限责任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,使用机器进行缫丝,规模虽小,却是我国第一个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,可谓乡镇工业的鼻祖。
震泽的蚕桑业在沦陷期间受到毁灭性的打击,桑园荒芜,两个丝厂俱被毁。解放以后恢复缓慢,直至1985年,震泽镇蚕茧产量跃增,突破1万担。继承传统,如今震泽蚕桑业再度繁荣,高科技之引入使产量增加,茧质提高,全镇缫丝厂就有3家。缫丝业还带动了绢纺业和服装行业的发展。
有人曾提问,震泽何以只出丝,不出绸?而盛泽则何以只出绸,不出丝?其实这种提法过于绝对化。
实际上,震泽确实出产过绸,如明崇祯《吴江县志》(稿本)提到震泽“昔织轻绫名药段(缎),今更织重,西绫之名特著”。又如清道光《震泽镇志》亦载“西绫出黄庄者名黄绫,质厚而文。后有庄绫、徐绫并以姓著。”显见震泽曾出过绫类织物。另一佐证是清乾隆年间徐扬所绘的《盛世滋生图》(又称《姑苏繁华图》)上,苏州闹市店铺的市招上清晰地写上“震泽绸”三个字。
至于震泽绸业的衰落,可以从民国《震泽镇志》(稿本)中见到“丝绸一业,据父老云,洪(秀全)杨(秀清)难后,因无绸行,渐归消灭。”也即太平天国期间的战争,导致当地绸行关闭,从而堵塞了绸之销售渠道。再说近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,因势利导逐渐走向地区行业分工,逐步形成丝市震泽和绸市盛泽,乃是社会进步,又是商品生产的必然结果。近代,震泽地区手工织绸仅存南部蠡泽、蠡西两乡,产量有限,销往盛泽庄面。
不过,震泽农村妇女则善于利用废茧捻成线,织成绵绸,或自用或出售。